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罕见病是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的0.65‰-1‰的疾病,国际确认的罕见病有五六千种,约占人类疾病的10%。目前在中国,罕见病没有明确定义。
大家通过冰桶挑战了解到渐冻症(ALS)。紧接着更多的罕见病被大家认识,而这些罕见病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月亮孩子”——白化病、“蝴蝶宝宝”——大疱表皮松解症、“企鹅”——遗传性脊髓小脑共济失调、“威廉宝宝”——威廉姆斯综合征……
但是有一种疾病,全中国不超过20例,不要说美丽的名字,甚至连一个汉语名词都没有。Denys-Drash综合征,一种极为罕见的先天性疾病,以肾病综合征为主要表现,伴有男性假两性畸形、肾母细胞瘤。多发生在两岁以内,很快进展至末期肾衰死亡。六间房“爱心公社”在偶然的机遇巧合下发现,中国不超过20例的患者中,一位不足四岁的孩子马添翼,正争分夺秒的与死神抗争,与这种疾病痛苦周旋。
我是女生,也是男生
山东聊城茌平县,一间不足三十平的房屋,与中国大多数农村房屋一样,低矮、落破、颓败,唯一不同的是,这里有短暂的幸福、快乐与痛苦。在去北京看病之前,夫妻俩带着小添翼居住在这个房屋中。小添翼年轻的母亲陈玉英说,当初出生的时候给大家说的是小女孩,现在又变成小男孩了,在村里没法给人解释了。由于夫妻两人受不了村里人的指点,在孩子几个月大的时候,就去县城打工了。这个租住的小屋子,给了一家三口短暂的平静,即使孩子时刻被病痛折磨着。
房屋中落着灰尘的物件平静、破败,孩子的玩具七零八落的躺在床上,透过玻璃窗阳光照射下翻滚的灰尘,似乎回忆着这一家三口曾经的平静与哀愁。在过去治疗的三年里,积蓄花光,债台高筑,家中双方苍老同样病魔缠身的父母已经无力帮助这对年轻的夫妻。

90后的母亲陈玉英回忆:儿子马添翼,出生在12年10月20日。记得19号那天下午,我像往常一样去妇幼保健院做产检,测了宫高体重验了血尿什么的,一切如旧,很正常。等到做最后一项胎心监护的时候,评分总是不及格,孩子胎动不好,然后去吸氧,再做,还是不行,又去吸氧,又做,这个过程重复到半夜了,还是不行,最后那医生说,明天来做个b超看看吧,晚上医院没有做b超的,然后我们就回去了。现在想想,当时真的太傻了,不知道换家医院去检查么!回去了这一夜真的不好过啊,担心孩子,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样了,就这样,躺一会儿,再起来坐一会儿,一宿都没睡。当时觉得时间过的好慢啊,那一夜那么难挨。
第二天,不得不剖腹产,可怕的预感一直围绕着陈玉英,孩子迟迟不见被抱来。直到下午,通过家人才知道,孩子已经被送进ICU,重症监控室。医生排除了其他疑似症状后发现孩子的两性畸形,没有发现子宫,也没有发现睾丸。
在中国的文化里,人们避讳的问题很多,尤其是性别。孩子是男孩,出生误当做女孩,但是,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全世界都知道孩子是女孩了,又怎么去贸然宣告孩子是男孩!特别是在中国的农村,即使大家再有同情心,也无法阻止别人去讨论,去指指点点。
纵使泪流满面,亦要面对
很多事情确实难以去接受,但为了保住小添翼弱小的生命。不管是两性畸形,还是肾病,只要他活着,就有希望有一个幸福的人生!按照医院的预约,带着小添翼做了染色体检查。然后就是等,等,等,漫长的等待。
得知染色体的结果,孩子不是两性畸形,孩子得的病也有了明确的定性与解释。明确了方向,意味着全国四处寻医的日子开始了。接下来,马不停蹄的跑到天津、四川、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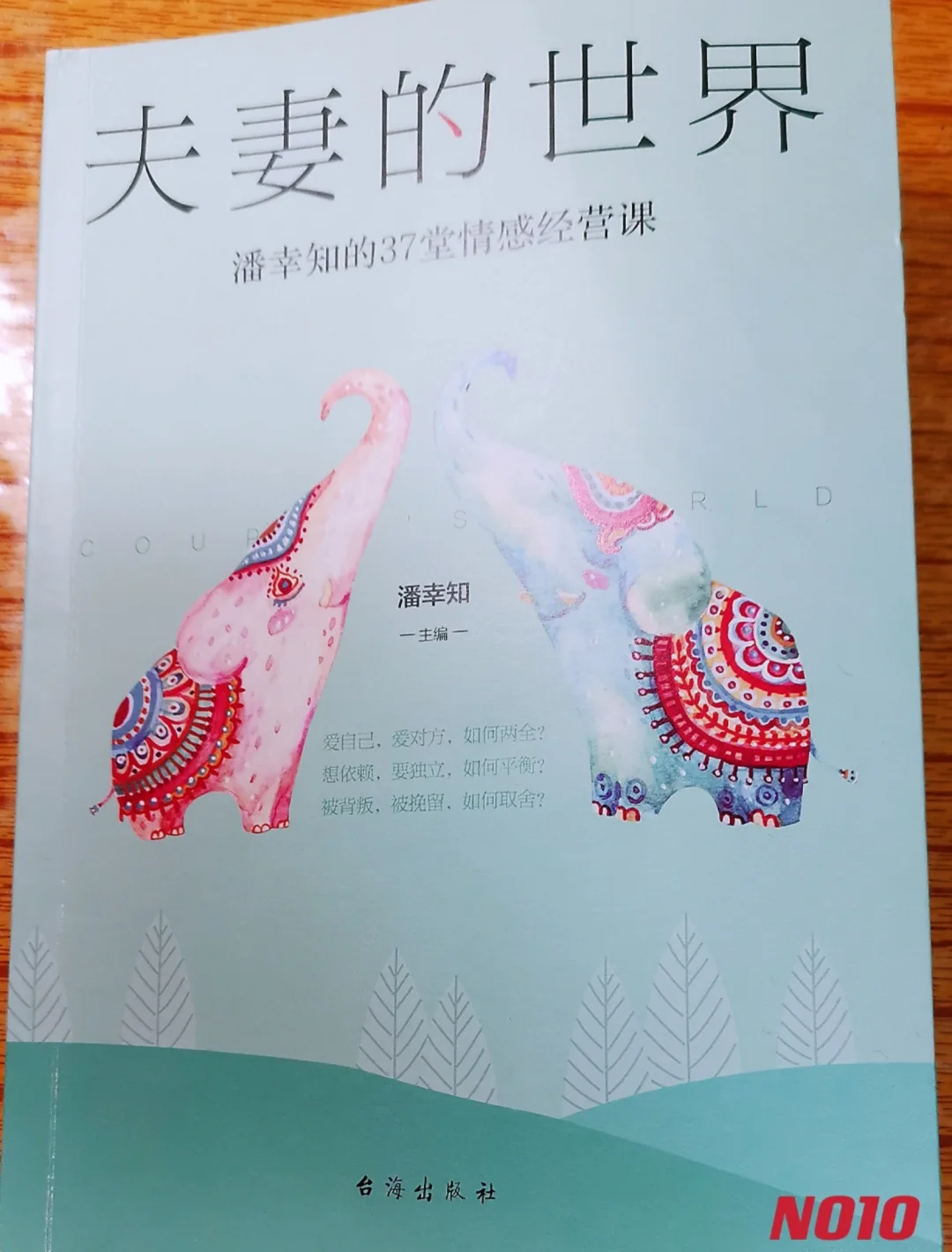
2014年2月25日,北大医院,抽取一家三口的血后,便是漫长的等待。这期间盼望着知道结果,又害怕知道结果,一次次播通北京的电话! 8个月过去了,最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小添翼的基因确实有问题, Denys-drash综合征!
鲁迅曾说: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小添翼身上的这种疾病,不是痛苦,而是灾难,比悲剧还要悲剧的灾难。大夫告诉他们,孩子唯一的希望就是肾移植,否则孩子过不去儿童期!
人在疾病面前,没有任何浪漫化的伪善,更没有伪装的浪漫。小添翼不得不接受身体一次次真实痛苦的人生事实,母亲与父亲也不得不接受让孩子幼小的身躯被各种针头、仪器折磨的事实。
“肿瘤不相信眼泪,不相信亲情,不相信决心,不相信实力。”一位目睹无数重症病例的中国医生感慨。很多如此的家庭基本都要经历一场身心俱痛的浩劫,一个人难以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的痛苦,如此情况之下就像是在地狱中呼唤天堂,在黑暗之中寻找光明。甚至是在人财两空之后,才能明白这句话在残酷背后的真实。
爱与被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在来北京治疗的这段时间里,陈玉英感到了拥挤,城市的拥挤与浮躁,人与城市的拥挤,物质与生活的拥挤,希望与绝望的拥挤,但是,如此的拥挤还是让她感觉一种被隔离般的孤独。她孤独之中的哭泣与人来人往的实际生活的对比,给六间房“爱心公社”每一位社员深深的震撼。
在最近一次看望他们的时候,六间房“爱心公社”社员目睹了这对夫妻居无定所的生活,吃穿住基本都在医院的走廊里。在北京这个一线城市里,吃穿住行成本极高,并没有向他们提供一个可以容身的地方,而这个现代化的都市也并没有给这样一个家庭表达痛苦和慰藉的渠道。
现代社会,人们沉浸在生命的喜悦与算计当中,高唱凯歌,前仆后继的歌颂强者。高速运转的大脑计算着每一天的得失与喜怒,如蚁附膻的崇拜着娱乐偶像,让一些处于极端情况下,需要得到帮助的人不得不孤独面对残酷命运与庞大、神秘的医疗机构,孤独者在不知不觉中做着泯灭孤独者的事。日本心理学家河合隼雄说,我们所做的一切,似乎就是为了逃避和淡忘不幸,哪怕是在讲给孩子们的童话中。
有一次,陈玉英见到六间房“爱心公社”一位社员的时候说道:辗转这么多医院和地区,一路走来,好心人帮助我们的太多了!阿贝尔.加缪在《秋,是第二个春天》中所说:我们听说过的责任只有一个,那就是爱。爱是一切故事中最美好的部分,别让这个还未感受过世界爱的幼小生命凋零。六间房“爱心公社”爱心行动连接(孩子母亲微博:爱翼宝得永生)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