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横空出世的《繁花》,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也将《上海文学》编辑金宇澄从文学的幕后带到了台前。这部娓娓用沪语摇曳出上海市井风情、饮食男女的别致作品,在评论界和市场上都表现亮眼,成为沉寂多年的当代文坛最重要的收获之一。而最难得的是,人们真正是从那绵密的、繁花着锦的独特文字里,认识并记住了金宇澄这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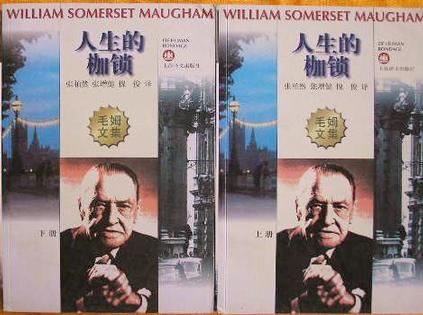
满纸繁花落尽后,金宇澄停下虚构的笔,转而写了一段真实的历史。主角是他的父亲和母亲,一对在革命时代中经历过血和牺牲的、却又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书写的姿态,是“回望”。与《繁花》的写作不同的是,这一次,作为书写者和儿子,金宇澄在这个过程中努力隐去了自己的声音,而让历史本身显影和发声。这种显影和发声,在当下未必有确凿和清晰的意义,只是,“记忆与印象,普通或不普通的根须,那么鲜亮,也那么含糊而羸弱,它们在静然生发的同时,迅速脱落与枯萎,随风消逝,在这一点上说,如果我们回望,留取样本,是有意义的。”
历史如何存在,并提供真实?《繁花》中,人物皆“不响”。《回望》中,金宇澄写道,“一切已归平静”。
在一切已归平静时回望
金宇澄的父母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两男一女,他是老二。1951年生大儿子的时候,因母亲的工作当时忙得不可开交,给孩子起名“芒芒”(忙忙);次年生二儿子的时候,因为生产舒服顺利,给孩子起名“舒舒”。
那段时间,是老金家难得的一段平稳时光。几年前,从事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父亲正出生入死;而三年后,父亲又被突然从家带走,接受了长达一年半的隔离调查。惊魂未定的母亲一边担心丈夫安危,一边咬牙用微薄的工资抚养一大家子人。
这一切,直到很久之后才再度平静下来。《回望》的第一章,就叫做《一切已归平静》。这篇文章初稿于上世纪90年代,2014年曾发表于《生活周刊》,置于卷首,正作为一个引子。“平静”,是一个儿子对父亲晚年的观视。一生在革命风雷中锤炼自己的父亲,老境到来时,喜欢和曾经的朋友、同志互相寄寄明信片,“讲无数旧话”,直到一个个友人离世。他还会伏在一部缩字本的《廿四史》前,用放大镜看那些小字。金宇澄情绪复杂地写道,“在漫长的人生中,已无法再一次寻找他年轻时代的神秘未来,只能在放大镜下,观看密密麻麻的过去”。
父亲于2013年去世。金宇澄找出父亲的书信、日记、笔记,以及关于父亲所在特殊系统的资料,择取、拼贴,添加进了自己对于父亲的观视和叙述当中,“远看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如何应对他的时代,经历血与牺牲,接受错综复杂的境遇和历史宿命”。这一部分内容曾以《火鸟——时光对照录》刊于《收获》,也成为《回望》一书的第二部分《黎里·维德·黎里》。
父亲走后,母亲情绪很差。金宇澄陪她翻看旧相册,向她问及往事。他请母亲以照片为序,记下曾经的时间和细节。近90岁的母亲认真地做了起来,废寝忘食,这件事让她内心平静。母亲的两大本剪贴,呈现出“一个上海普通女孩的时光之变”。她的口述,成为了书的第三部分《上海·云·上海》。
书里有一处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父亲的橱柜里,一直摆着他和母亲的合影。照片是两个人在太湖的留影,彼时,28岁的父亲在《时事新报》当记者,20岁的母亲在复旦中文系读大二。“他们那时年轻,多有神采,凝视前方的人生,仿佛无一丝忧愁。他们是热爱生活的一对。”任何看到这张照片的人都会被他们脸上那种被时代照耀的神采奕奕所打动,但其实,在拍摄这张照片的岁月里,父亲奉命回苏北根据地接受审查,而母亲想奔赴北方参加革命,令她的资本家哥哥大惊失色,将她从即刻开动的火车上拖回来,关在家里一个月。
父亲(二十八岁《时事新报》记者)与母亲(二十岁,复旦中文系大二)在太湖留影,1947年4月7日
母亲说父亲“从不讲自己的痛苦,说一切已经过去了,不能再讲了,很多人都死了……”但讲述者都知道,既有“回望”,这一行为本身便不可能留下现世安稳岁月静好。正如那张照片的暗示,平静之下,是无法忘却的风暴历史。
黎里的维德,上海的云
在儿子的书里,父亲的故事,叫《黎里·维德·黎里》;母亲的故事,叫《上海·云·上海》。两部分标题十分对仗:“维德”是父亲从事地下工作时的化名,后来母亲也一直这样叫他,而“黎里”是维德的故乡江苏吴江黎里镇;“云”则是母亲初二时为自己改的单名(多年后她想起来,觉得这个字有彷徨无定之意),她生长在上海,家里开着银楼,是资本家小姐。
原本平行的两个人,在特殊的时代中,在彼时交织着革命与浪漫的上海,并不令人意外地产生了交集。

从黎里古镇走出的父亲,思想先进,一从学校毕业就加入了中共秘密情报系统。他的经历,其惊心动魄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下的谍战剧,却绝没有谍战剧里那种理论上的安全性与正确性。在上海工作时,他以“程维德”之名,和另一党员程和生假扮兄弟。1942年,因著名的“佐尔格案”的连锁效应,日共某组织暴露,供出了一部分上海情报人员,其中就有“胞兄”程和生。日本宪兵冲进房间,不见“哥哥”,抓走了“弟弟”。维德在经历反复拷问后,没有暴露自己和组织的身份,但以“妨碍社会罪”被判刑七年,先后囚于日本宪兵监狱和汪伪监狱。
他被抓后,祖父从黎里赶来杭州探监。直到晚年,父亲还清楚记得那心酸的一幕。两人四目相对,祖父看了儿子半晌,一直叹息,开口讲的第一句话是:“倷戆伐?”(“你傻呵?”)后来他才知道,为了筹钱来杭州看自己一眼,祖父受了不少委屈,回到黎里就卧床不起,因无钱买药,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世界。
在组织帮助下,父亲以“保外就医”之名出狱。尽管遭受了病痛折磨,但他依然充满活力,依然担任着情报系统的重要一环,衣着考究地在上海滩的咖啡馆里寻找接头人。
和父亲的传奇人生相比,母亲的经历便单纯多了——然而并不简单。外祖父的“老宝凤”银楼在虹口颇有声名和收益,她从小衣食无虞,在学校里也是上进的好学生,思想进步,参加戏剧社,酷爱读新文学。1945年夏秋之际,正逢日本投降的万众欢腾中,她中学毕业,考上了私立复旦大学中文系,并在朋友家里认识了陌生男子程维德。她对他的第一印象是,“觉得他英俊端正,只是个子稍矮些”。那时,维德已是“老革命”,在报社工作,写一手好文章。两个时髦的人互有好感,常常在“吉士”咖啡馆约会。
母亲16岁,淡绿色旗袍,新式低领纽扣,那时她已改名为云
沪西大自鸣钟,母亲在外祖父家顶楼晒台上
上海解放后,母亲选择从复旦肄业,参加了华东军政大学的短期训练班。1950年回上海,和父亲一起在上海总工会工作,两人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此后的岁月,伴随着“运动”、“学习”、“肃反”、“下放劳动”这些关键词,这一对夫妻的工作生活,牢牢印合着大时代的车辙。
父母留影于黄浦江船中,也在此时,组织上批准他们结婚。
1955年,父亲突然被从家带走,上面说是去北京出差,谁知一去无确切消息,夫妻仅能靠有限的通信来维持。终于有一次,担忧而敏感的母亲发现,丈夫信中写到“天降暴雨,突发惊雷”,和当时上海的天气一样,方确信父亲就在上海,被人隔离,不能回家。但尽管如此,她还是按捺住疑惑,在回信中向父亲讲一些家长里短,讲兄妹三人的成长细节。一个28岁的姑娘,一个年轻的母亲,在特殊的年月里,只能用隐忍的方式来熬过心理的痛楚,等待和家人的团圆。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他们如何处理属于个人生存的问题,才是最产生意义的部分。
“我常常入神地观看他们的青年时代,想到属于自己的青春岁月。”金宇澄如此写道。1969年初,他和哥哥金芒去黑龙江嫩江农场插队落户,在给父亲的信里,他多次描述大批犯人在眼前割麦的情景。但父亲在复信里,对他的这些“震惊体验”都不予回应。一直到了他重新回望父辈历史的时刻,见到密密麻麻的通信、报告、资料后,才明白其实自己当年强调的那些内容,父亲早已懂得。而母亲也和自己一样,在年轻的时候下农村劳动,做过那么多繁重的农活。——历史给予每一代的经验时常相似,并得以贯穿其中,令每一代人都不能自外地去观看。
不标准的“非虚构”
《回望》一书附有许多特别印制的旧照片、旧资料等,手感粗糙,仿佛历史的触感。还有一张金宇澄的手绘上海地图,标出父母曾居住、工作过的地方,共有三十处之多。
金宇澄手绘图
这本书共四章,共用了三种叙述文体。父亲的记录和资料,母亲的口述,金宇澄自己的叙述和观察,三者交汇,从那些七嘴八舌的声音和画面中,仿佛听得见历史的喧哗声。这种喧哗,有时甚至互相龃龉,几相对照,能清晰照见谁的记忆不完整,甚至出了差错。但金宇澄没有去纠正这些不一致的痕迹,他刻意留在那里,保留了“现场感”,也保留了某种“寻找”的姿态。
从本质上说,这是一部近些年十分流行的“非虚构”,但从形式上说,又和别的非虚构十分不同:相较之下,它的文体显得太杂乱,并且它讲述的故事,尤其是父亲的故事,常常显得“未完成”。读者从头至尾都被父母青年时代的风雷激荡着,但最后发现留取最深印象的,却往往是一些片刻的细节和情绪,它们无法被归拢为一处——譬如会突然宕开一笔,花很大篇幅写一位父亲童年玩伴的家庭乱伦悲剧,这件事其实和父亲崇高的事业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细若游丝的牵系,大概便是父亲对黎里的和往生者的追思,以及对人性之复杂性的洞见。然而有意无意置于此,令人读后唏嘘不已。
金宇澄承认这不是一个“标准的非虚构文体”或“人物传记”。在他的关于父母故事的叙述里面,在“意义”和“意思”之外,余有许多的空白,有充沛资料则写,无则不写,并不刻意将这些空白填补弥合起来。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始终保留着对于“文体”的最大兴趣,那种“七嘴八舌”的材料杂糅,或可显现一个典型的小说家而非典型的调查记者、传记作家、非虚构作者等面对和处理历史真实的方式。
金宇澄说,他向来不太爱看头头是道或者前后逻辑性非常强的历史,反而特别喜欢钟爱一些细节、一些灵光一现的段落。陈巨来的《安持人物琐忆》、李伯元的《南亭笔记》都是他常常谈及的书,那种“灵光一现”里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世界观。在《回望》一书的北京发布会上,他一坐下来,并不讲父母如何如何、写作如何如何,而是笃笃定定地一口气讲了好几个来自各类私家历史记录中的传奇故事。“这样的小小短章、短的叙事,反而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想象空间。所以我在《回望》里面有的时候会触及到一些小的细节,或者说,这些细小的部分才是我感兴趣的。”
“人与群的关系,人与史的碰触,仿佛一旦看清了某些细部,周遭就更是白雾浑茫……万语千言,人只归于自己,甚至看不清自己。”最后一节《我们回望》里如是写道。这些“细部”,容易风化,容易被遗忘,但它们又往往会成为个人最值得珍藏的样本。
· END ·
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布客君坚持原创给你看
如果你喜欢,就赞一下呗~
长按指纹
关注布客帮
更多精彩请关注北京晚报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